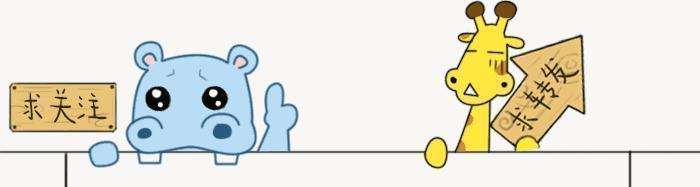二姨的院子里有两株树。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,却是杏树……
枣枣的品种,是“马奶子”枣,长形,纺锤状,头部收紧,腹部饱满,因形而名。每到成熟的季节,摘枣算得上家里的一项“工程”。

因为如果爬上树用手摘,一是树木已很高大,果实密布,又多生于尖梢。人上去不安全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,就是枣树上生长着一种我们叫做“混混儿”(学名“刺娥”)的特殊的爬虫,黄绿相间,带有“警告色”的身体,一看就不是善茬。最为醒目的,就是它的背部清晰而规则地长着两排高耸的毛刺,不仅令人生理“膈应”,而且如果被它挨上,那份“酸爽”不亚于被马蜂蛰,受伤部位会立即肿起,好几天又痛又痒。

所以姨父每年都要专门拼接一个长长的杆子,用来“梆”枣。杆子到处,枣叶的悉索之后,便听得一枚枚枣子毕毕剥剥落地的声响。那时候姨父常会一边打枣,一边嘴里念叨着直到现在还记得的一句话:有枣没枣打三杆子……(形容做某件事不管有没有效果,先干了再说)。马奶子枣熟而不老、硬硬的时候最好吃,一咬嘎嘣脆,甜甜的枣香沁满口腔。
杏那棵杏树也不平常,结的是大白杏。每到成熟的季节,黑褐色的枝桠,片片的绿叶间,掩映着一枚枚饱满硕大的白色杏子,如同一幅立体的工笔画,线条清晰、层次分明、灵动诱人。

二姨总能在它长到最恰当的时候摘下来,用两手轻轻一掰,沙沙的杏肉便就此分开,深棕色的杏仁自行剥离,将其中一瓣放入口中,即糯且弹,酸甜交织,美妙无比。二姨看我“好这口”,每到杏子成熟时一定是“她来摘下我先尝”。
在我回县城上学的第一个秋天,二姨专门捎信来,嘱咐让我一定放了秋假(那时候县城的孩子许多家在农村,为了秋收所以县里的小学有“秋假”一说)回去吃。我自然是满口答应。没想到那一年最终没能回去,原因现在想不起来了,反正是当了一回“白眼狼”。
只记得另一位亲戚来到县城家里串门时偶然说到,二姨为了能让我吃到新鲜的杏,一再推迟摘果的时间,自己也舍不得吃,就那样一直等,直到最后许多杏子熟透了掉落在地上,已经软烂到将近腐败,二姨和姨父才不得不吃掉。
椿其实,二姨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香椿树。
它在我的记忆画面里,总是与一种主食——“冷汤”——同时登场。当地的“冷汤”,其实就是煮面条。后来我边回忆边分析“冷汤”的得名,有所心得:我们那里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白面是稀缺之物,通常只在盛夏才会偶尔吃几次,需要自己用面粉加工成面条,煮熟后伴上作料“服用”。
刚煮出来的面条太烫,为了降温,定要用“井拔凉水”——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——浸泡,刚出井的水的那份凉,沁爽宜人,但又绝无现在冰箱致凉的生硬伤人。这样一碗面条,便兼具了饱腹与消暑的两种“功效”。“冷汤”当是因此得名。
家里条件有限,用以拌面的作料,既不是现在的炸酱,更没有肉丝打卤。而是用少许香油入花椒爆香,趁热淋在碗中的虾皮之上,“刺啦”一声之后便是四溢的鲜香。再加酱油和食盐,便成那时吃面条时唯一的拌料——“花椒油”。
一切停当之后,现在想来堪称“奢侈”的一幕便会上演,二姨端着给我拌好的面碗,来到香椿树下,挑选最为鲜嫩的芽尖,直接掐入碗中,一碗朴素、绿色、每一份食材都极尽那个年代特有的纯香的农村“冷汤”便告完成。
工作以后,我吃过了京南的“五卤面”,天津的“百卤面”,苏南的奥灶,苏沪的阳春,镇江的锅盖,四川的担担,兰州的牛拉、山西的刀削,西安的biangbiang,新疆的拉条、武汉的热干,河南的羊烩,广东的龙抄、日本的豚骨、意大力的洋粉……但总觉得差点什么。差“井拔凉水”?还是自然生长的香椿原香?大概还是差了摘下香椿叶拌入我碗中的那双粗糙的手吧……
(未完待续,敬请期待)
前一篇链接:“舌尖”上的童年(连载二)
后一篇链接:“舌尖”上的童年(连载四)
-
揭秘网上流传的拉酒线骗局,真正辨别酒的品质还需品尝
2024-12-30 -
一方砖的大美天地,“万岁不败”古缘阁藏汉砖展
2024-11-08 -
ZLZB-7微电脑智能综合保护装置
2024-11-22 -
902荧光之王你收藏了吗
2024-12-04